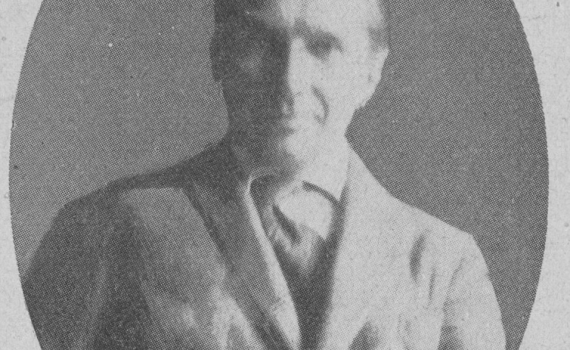
為什麼還沒有舉行全球首演?
Category : 表演 | Auff cn
https://de.wikipedia.org/wiki/Walter_Dahms
Hamburg Staatsbibliothek https://resolver.sub.uni-hamburg.de/kitodo/PPN774616555_0016
[pgc_simply_gallery id=”221″]
沃爾特·達姆斯 (Walter Dahms) 於 1912 年撰寫了一篇有關這部歌劇的詳細文章。
尚未進行完整舞台表演的原因(仍需 2026 年!)如下:
當我第一次拿起葛普法特《薩拉斯特羅》的鋼琴改編版時,我被創作者的大膽所震撼,他竟然能為我們這個時代呈現如此簡潔、清晰、毫不含糊的作品。誠然,這部作品的構思和創作是為了紀念1891年的莫札特誕辰。但當時最不幸的動亂(尤其是印刷工人大罷工)使得原定在德勒斯登和布拉格的演出泡湯。第二年,一切都太遲了。因此,《薩拉斯特羅》至今仍未上演[作者註: 1912年]。如果由那些善良的德國人來決定,因為他們從自己鍾愛的報紙上對創作型藝術家知之甚少,那麼這部作品或許會永遠無法上演。但如果極度片面、自私自利的新聞業在創作人才和輕信的公眾之間築起的惰性和惡意之牆無法在某個時刻被打破,那將是多麼令人遺憾。這種嘗試是值得的,既有教育意義,又有前景。
卡爾戈普法特的音樂劇《薩拉斯特羅》
作者:沃爾特·達姆斯
如今,誰聽到一部名為《魔笛(下)》的作品時不會豎起耳朵呢?我們談論和撰寫了太多關於莫札特的言論,稱他為當今音樂危機的救世主,是帶領人們走出現代低效荒漠的領導者。 「回歸莫札特!」人們高喊。魏因加特納卻說:“不,前進到莫札特!”無論人們如何解讀,有一點是肯定的:音樂和戲劇藝術的進一步發展絕不會是“超越瓦格納”,而想要創作出罕見、持久而又新穎的作品的舞台作曲家,必須從瓦格納之前的某個時刻開始。因為通往偉大而崇高藝術的目標,還有許多未曾踏足的道路。
當我第一次拿起葛普法特《薩拉斯特羅》的鋼琴譜時,我被作曲家的勇氣所震撼,他竟然能為我們這個時代奉獻如此簡潔、清晰、毫不含糊的作品。誠然,這部作品是為1891年莫札特誕辰紀念日構思和創作的。但當時最不幸的動亂(尤其是印刷工人大罷工)使得原定在德勒斯登和布拉格的演出泡湯。第二年,一切都太遲了。因此,《薩拉斯特羅》至今仍未上演。如果由那些善良的德國人來決定,因為他們從自己鍾愛的報紙上對創作型藝術家知之甚少,這部作品或許會永遠無法上演。然而,如果極度片面、自私自利的新聞業在創作藝術家和輕信的公眾之間築起的惰性和惡意之牆無法在某個時刻被打破,那將是多麼令人遺憾。這種嘗試是值得的,具有啟發性,同時也很有希望。
《薩拉斯特羅》在我初聽時便給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溫這部作品,對它的興趣與日俱增。這部作品最終追求的,與現代人所鍾愛和推崇的截然不同。它並非旨在厭惡我們人類的原始情感(就像當時流行的真實論者及其德國追隨者那樣)——不,它旨在提升我們原始情感的境界。它純粹、樸實、健康──簡而言之,它以一種強烈、感傷、催人淚下的幸福感,如同病態的爆發,既有語言的,也有音樂的。因此,我現在要為這部作品寫一些警示,因為身為音樂家和評論家,我堅信它必然也會影響到其他所有能夠接受高尚事物的人。
整部作品都充滿象徵意義──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的鬥爭。莫札特的《魔笛》也體現了這種傾向。它是一種抗議,對當時維也納的知情人士來說,這不難理解,它抗議的是各行各業的惰性、墮落和良知的壓制。它不帶任何人道主義的浮誇,而是試圖宣揚人類普遍博愛的理想。 (然而,即將到來的法國大革命卻為這種理想帶來了強烈的不和諧音——這同樣是一種博愛,但又有所不同!)。當時,人們的目標是塑造那些在命運的考驗中被淨化的人物。火與水僅僅是像徵。然而,光明與黑暗、薩拉斯特羅與夜後之間的鬥爭並沒有在《魔笛》中上演。劇終部分指向了即將到來的時代,一個充滿鬥爭和衝突的時代。
歌德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他策劃並起草了薩拉斯特羅戲劇《魔笛》的第二部分,並將其改編成歌劇文本。格普法特的作品以此為基礎,其詩作由戈特弗里德·施托梅爾創作。歌德續寫《魔笛》是合理的。兩種對立的基本力量(大致象徵為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戰鬥必須在某個時候解決。歌德的提綱為格普法特和施托梅爾提供了戲劇指導。莫札特的音樂必須在某些時候保留某些旋律和主題。結果必須是和好的:愛必須戰勝恨。同樣必要的是透過歌德想要的衝突來實施共濟會的思想。歌德續寫《魔笛》的合理性是毫無疑問的;當人們見證了透過完美執行 Goepfart-Stommel 工作實現既定目標時,人們會無條件地、高興地肯定它。
審視《薩拉斯特羅》會發現,其幕幕結構蘊含著其獨特的本質。第一幕包含開場白,將我們引向戲劇的各個世界:善的世界(薩拉斯特羅)、惡的世界(夜後)以及原始人性的世界(帕帕吉諾)。在《魔笛序曲》莊嚴的開場之後,祭司們的集會拉開了帷幕。每年,他們都會派遣一位兄弟來到人間,見證人類的苦難與歡樂。塵世的朝聖者回歸純潔,這一次,他的命運落到了他們的領袖薩拉斯特羅身上。他從中領悟到了一個特別的暗示:「神明在危險中接受考驗!」他知道,一項艱鉅而偉大的使命正在等待著他。他必須戰勝宿敵──夜後,那位原始的邪惡。只有他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他憑藉著更高的精神修養,看透了她的意圖,而她卻看不透他。莊嚴而嚴肅的基調貫穿整場演出。持續的節奏、清晰的和聲以及深沉而深情的旋律貫穿始終。至此,《薩拉斯特羅》與莫札特的歌劇一樣,是聲樂歌劇。這也使得這部作品在現代歌劇文學中佔有特殊的地位。管弦樂團並沒有決定性的發言權;它只是提供了氛圍,可以說是音樂事件展開的土壤。
第一次轉變將我們帶入夜後的國度。這是一個對比鮮明的人物刻畫。跳躍的節奏立刻傳達出這片國度中瀰漫的細微動亂。如同薩拉斯特羅一樣,女王也出現在她的戰友之中。摩爾人莫諾斯塔托斯,他的女兒帕米娜在《魔笛》中逃脫,如今他侍奉並愛著母親,他向女王報告,對光明國度的複仇行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塔米諾和帕米娜的孩子,國王的兒子,被鎖在金色的棺材裡,只有他們的黑暗力量才能打開棺蓋。象徵性地:新時代被羞於見光的精靈所奴役。女王勝利的嚎叫揭示了她內心對高貴的薩拉斯特羅的反抗。他與她的鬥爭是多麼正義啊!
第二次變形展現了塔米諾和帕米娜對愛子的深切關懷。塔米諾對孩子的擔憂與日俱增,導致他再次陷入母親——夜後的影響。夜後試圖說服他向薩拉斯特羅復仇。但這對薩拉斯特羅來說卻是一種誘惑,她安慰他,承諾孩子未來將肩負偉大的使命。女聲唱詩班溫柔抒情的歌聲伴隨著棺材的無情搬運,誘惑場景中的音樂逐漸增強,最終引向宏偉而原始的祭司合唱“誰將狂熱地對抗光明?”
第三次蛻變展現了帕帕基諾和帕帕基娜所代表的無拘無束的自然人的生活和活動。在孩子們歡快的喧鬧中,在歡樂和玩笑聲中,奧羅拉——眾神的恩賜——誕生了。她是人民的孩子,注定要救贖王室的兒子。優美寧靜的音樂伴隨著這一蛻變。幾首莫札特式的旋律響起。生命的潮起潮落生動地、永不枯竭地流淌,筆觸簡潔有力,精準有力。
第一幕為戲劇鋪墊,第二幕則以敵對勢力的爆發將戲劇效果推向高潮。薩拉斯特羅忠於神聖的使命,踏上了塵世之旅。在這裡,他遭遇了他的宿敵。光明與黑暗兩大元素力量的命運得以實現。王后並未認出這位流浪者。未知的魔力將她吞噬,使她對他燃起熾熱的愛火。她試圖將他拉攏到自己的目標中,而所有這些目標都以毀滅薩拉斯特羅為根本目標。當她發誓要將國王的兒子菲比斯從金棺中解救出來,使他復活時,他最終同意協助她除掉薩拉斯特羅。薩拉斯特羅意識到,他必須做出犧牲才能戰勝王后,開啟「新時代」。他的人格和懺悔中蘊含著非凡的道德力量。格普法特的音樂與詩人一樣,在建構和演繹這精湛的戲劇中堪稱完美。他完全憑藉自身才華,其旋律和獨特創意的源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以簡潔的筆觸傳達對比。他的音樂語言充滿戲劇張力,震撼人心,令人回味無窮,卻又獨具匠心,令人耳目一新。他對情感表達的自信隨處可見。值得注意的是,夜後在看似勝利的氛圍中,首次在劇中運用了華彩,彷彿出於內心的渴望。在這裡,華彩成為了一種真正的表達方式——一種真正必要且能夠緩解緊張的表達方式。
第三幕的效果參差不齊,這是由一系列必要的結局疊加造成的。這在戲劇文學中並不常見,我們發現,在衝突的延續和解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角色(奧羅拉和菲比斯)只在第三幕出現。第三幕自然主要包含莫札特式的主題。引用莫札特的部分原因是歌德的註釋。因此,奧羅拉伴隨著《魔笛》中的鐘琴音樂登場。無需解釋,因為這裡除了莫札特的音符之外,聽不到其他音符。在個別樂段中,格普法特使用了莫札特常用的音樂迴旋曲式。他必須保持這種風格。我們不應該說他引用莫札特的音樂是為了讓自己輕鬆自在。相反,為了讓整部作品不致於崩塌,讓自己的感受力適應莫札特的風格和精神,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他本可以用自己創作的歌詞來代替這些引文,但他正確地認為,在那些特定的段落中,莫札特的表達是唯一可能的表達。
第一幕將我們帶回森林中的原始人。奧羅拉釋放了福玻斯,從而將普羅米修斯的神賜歸還給了人類。劇情高潮是兩位象徵性人物之間最親密的愛情場景。接下來是一場滑稽的戲,可以說是一場盛大的狂歡,伴隨著迷人而獨特的芭蕾舞音樂。
第一個變形展現了塔米諾王宮的一段宮廷生活。淑女紳士們正為最新消息爭吵不休。這場毫無意義的爭論隨著最新消息的宣布而結束:獲救的王子菲比斯攜奧羅拉入宮。由此開啟了末日的序幕。一個新時代由此誕生。葛普法特為宮廷成員的對話找到了令人愉悅的基調,這些基調展現了他作為音樂幽默大師的風采。
一場公開的轉變引領著終曲。在這裡,最鮮明的對比出現在年輕王子夫婦入場時的歡呼雀躍與祭司們對薩拉斯特羅之死的悲痛之間。這兩個場景只能用受莫札特影響的主題來演繹,例如《魔笛》終曲中歡快的合唱,以及C小調的《火與水的音樂》。隨著劇情的推進,例如夜後的到來,她也出現在舞台上慶祝勝利和歡騰,格普法特找到了自己獨特的、極具特色的風格。劇情發展成一場災難。夜後要求見她死去的敵人:「如果我的王國淪為廢墟!」塔米諾帶她來到薩拉斯特羅的石棺前。當她認出屍體裡的流浪者時,她昏了過去。同時,莫札特不朽旋律的《啊,伊西斯與歐西里斯》在所有祭司的齊聲吟唱中迴盪,誓言即使在薩拉斯特羅死後,也要繼續在他的靈魂中工作。王后被降臨的可怕現實(她自身的失敗)所震撼,表達了渴望進入崇高愛情紐帶的強烈願望,但卻遭到祭司們的憤怒拒絕。在痛苦之中,王后呼喚化身的薩拉斯特羅(她的敵人和朋友),祈求他給予她和解的徵兆,並滿足她的願望。這確實發生了。一位神靈出現,用和平之手觸摸王后,將她帶入永恆和平的境界。薩拉斯特羅和王后在穹頂上合而為一——愛戰勝了恨。有了愛,一切邪惡都被根除。如今,統治家族和人民帶著截然不同的喜悅,加入了透過愛獲得解放的歡呼合唱。
格普法特-施托梅爾的《薩拉斯特羅》展現了其道德意圖和純粹偉大意志的精髓。這種能力與意志的同步性在其詩歌和音樂中清晰可見。德國歌劇院必須確保這樣嚴肅而精湛的作品成功。他們的責任是將這部作品推向大眾,使其在崇高的理念、簡潔有力的構思和執行中脫穎而出,使其憑藉內在的簡潔和真實在當代創作中佔據著非凡的地位,並且——我堅信——它將永遠給人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以格普法特的《薩拉斯特羅》開場的德國舞台,將享有真正的藝術成就的美譽。